自AI技术进入影视领域以来,圈内可谓每天都迎来一次“震动”,而Seedance 2.0大模型的问世,再度掀起轩然大波。
新模型上线后,海量用户第一时间上手体验,有人称它为“视频界的Nano Banana Pro”,也有人认为它已超越Sora 2。网友纷纷将自己的创意“投喂”给AI,惊喜地发现生成效果远超预期。威尔·史密斯诡异吃面条的时代已成为过去,随之而来的,是人人可独立制作精品的极致生产力。
然而,技术革新带来的震动远不止“喜悦”。过去,许多人认为AI将最先冲击工业人工劳动力,没想到率先步入“蒸汽时代”的,反而是影视行业。

有人将Seedance 2.0的迭代视为机遇,也有不少人深陷恐慌与焦虑。技术更新催生出多元化声音,为此,骨朵分别与由传统影视美术转型为AI内容创作者的吴磊、从长剧编剧转型为AI动画导演的哈尼,以及一位传统影视行业的导演兼编剧小花(化名),聊了聊他们的看法。
史诗级更新来了?
几天前,吴磊正在制作一部国潮风格的春节祝福短片。Seedance 2.0上线后,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将已经完成的图片输入新模型,没有附加任何提示词。结果令他惊讶:模型仅通过图片中人物的服饰与姿势,便完美演绎出正确的舞蹈风格,传统乐器的指法手势分毫不差,还自动配上了合适的音效。
“另一个惊喜是人物对白”,吴磊回忆道,“模型能自动捕捉正确人选,配以适合其年龄、性别的音色,甚至自动给对方切换特写镜头,完成镜头组合。”更让他感到“可怕”的是,当画面中出现新春祝福文字时,模型竟自动配上了家喻户晓的春节背景音乐。

吴磊使用Seedance2.0大模型生成镜头
同一时间,哈尼第一次将原创小说直接喂给Seedance 2.0。一个完整的影视级分镜成片在极短时间里出现了:人物设计从头到尾保持统一,场景连贯,甚至剪辑节奏都有了呼吸感。
那一刻她意识到,过去繁琐的流程——从小说改剧本、做人设场设、生成资产、出分镜表、抽卡试错到剪辑合成——被彻底改写了。“以前大家会骂AI‘听不懂人话’,”哈尼说,“现在SeeDance模型2.0终于懂得了影视级别的‘视听语言’,它开始拥有‘戏感’了,看得出没少吞影视作品来训练。”

哈尼使用Seedance2.0大模型生成镜头
两位创作人一致认为,此前的Sora 2虽技术出色,但对中国创作者并不友好:国外模型难以理解中国文化符号,使用门槛高、费用贵。虽然他们都强调各类AI工具的各有所长,但新模型的上线显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。
它真正把视频生成从“盲盒抽卡式尝试”拉到了工业级批量生产的阶段。
哈尼给出了直观的量化对比:素材可用率从过去的40%跃升至80%,“直出内容如果参考红果漫剧收剧标准,基本能达到C和B级,路人能看下去”。Seedance2.0大模型下生成的影片,懂得智能调节机位,分镜设计具备了连贯的“戏感”,“看起来不突兀”。
吴磊则从题材边界的变化来印证这种完整感。过去的古装玄幻题材,只能尽量设计无肢体接触的“魔法攻击”来规避AI的短板。如今模型不仅能处理拳拳到肉的武打动作,还能基于近景、特写自动完成15秒内的镜头组接。更令他感到预示性的是四种模态的交叉补足能力:“模型接收到一部分信息,就能自动补足生成其他与之匹配的合理内容。”
他将这种能力归结为导演思维与分镜思维,并大胆设想:“AI从完成单一指令的简单思维,变成了全方位自主性理解和完成任务——这是否会是未来‘全能AI剧组模型’的雏形?”
不过,两人也都谨慎地给这种惊叹划定了边界。
哈尼坦率地划分了应用层级,“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省掉粗略分镜、抽卡试错和粗剪,直出影片确实能直接使用;但要求高时,精细资产设计与人工精修剪辑仍是必需。”她强调,最大的门槛不是软件操作难度,“是创作内容、写故事、写剧本,以及理解剧本的能力。技术制作人员必须懂内容,否则AI跑出来的东西,只是一堆精美的PPT。”
吴磊的判断更为审慎。他认为现阶段Seedance 2.0还无法无缝融入传统院线电影和电视剧的制作流程,核心障碍有两个:一是输出视频精度尚未达标,二是目前限制了真人素材的使用功能。但与此同时,他对AI漫剧、短剧、广告领域的应用前景非常乐观。
Seedance 2.0带来的是影视工业底层逻辑的迁移,AI学会了视听语言,接下来要看创作者能否用好这门新语言,而不是被它淹没。
谁被洗牌,谁在逆袭
“很多人说AI现在是‘都说有金子,都在做铲子’,好精准。”小花这句略带戏谑的感慨,恰好点出了Seedance 2.0问世后影视行业的焦虑与亢奋。
当模型真正具备了导演思维与分镜意识,从业者们发现,AI浪潮下的所有传统影视行业岗位都会被整合和重组,都存在被替代的风险。这不是危言耸听,它最先发生在从业者自己的工种上。小花用“非遗手工作坊”来比喻未来的职业形态:当AI接管了大部分执行工序,“未来的创作者会是编导一体,有美术思维和独特的美学风格就够了。”
吴磊的体会更为具象。作为影视美术从业者,他目睹了传统工作流程的断裂。“整个美术部门人员大幅缩减,概念图、施工图、场景搭建、道具制作、环境布置——这套延续几十年的线性工序,在AI时代已不再适用。”美术的核心任务依然是完成剧本的视觉化呈现,但完成的方式,不再需要一钉一木。

吴磊使用Seedance2.0大模型生成镜头
淘汰的潮水紧随其后,最先漫过的是那些依赖信息差与人情链的岗位。
哈尼试用完2.0版本后,第一时间给做剪辑的朋友发了条消息:“你不能再只当剪辑了,立刻朝AI导演方向发展。”她并非预言剪辑师的工种会消失,而是强调单一技能正在贬值——传统剪辑人员懂影视、懂节奏,恰恰具备转型的最佳底子。
而真正面临灭顶之灾的,是那些不懂剧本、不会写和讲故事的导演。小花没有留丝毫情面,“AI只是加速了他们的退位而已。”她甚至从题材维度给出了一个干脆的判断:“男频将被AI直接取缔。男频观众只想看强剧情、大特效,无所谓人物魅力,AI将数亿的特效费全省了。”而女频因涉及情感投射与追星心理,AI能否真正取代仍有悬念,但也存在一个略显讽刺的事实,“现在很多流量明星的演技还不如AI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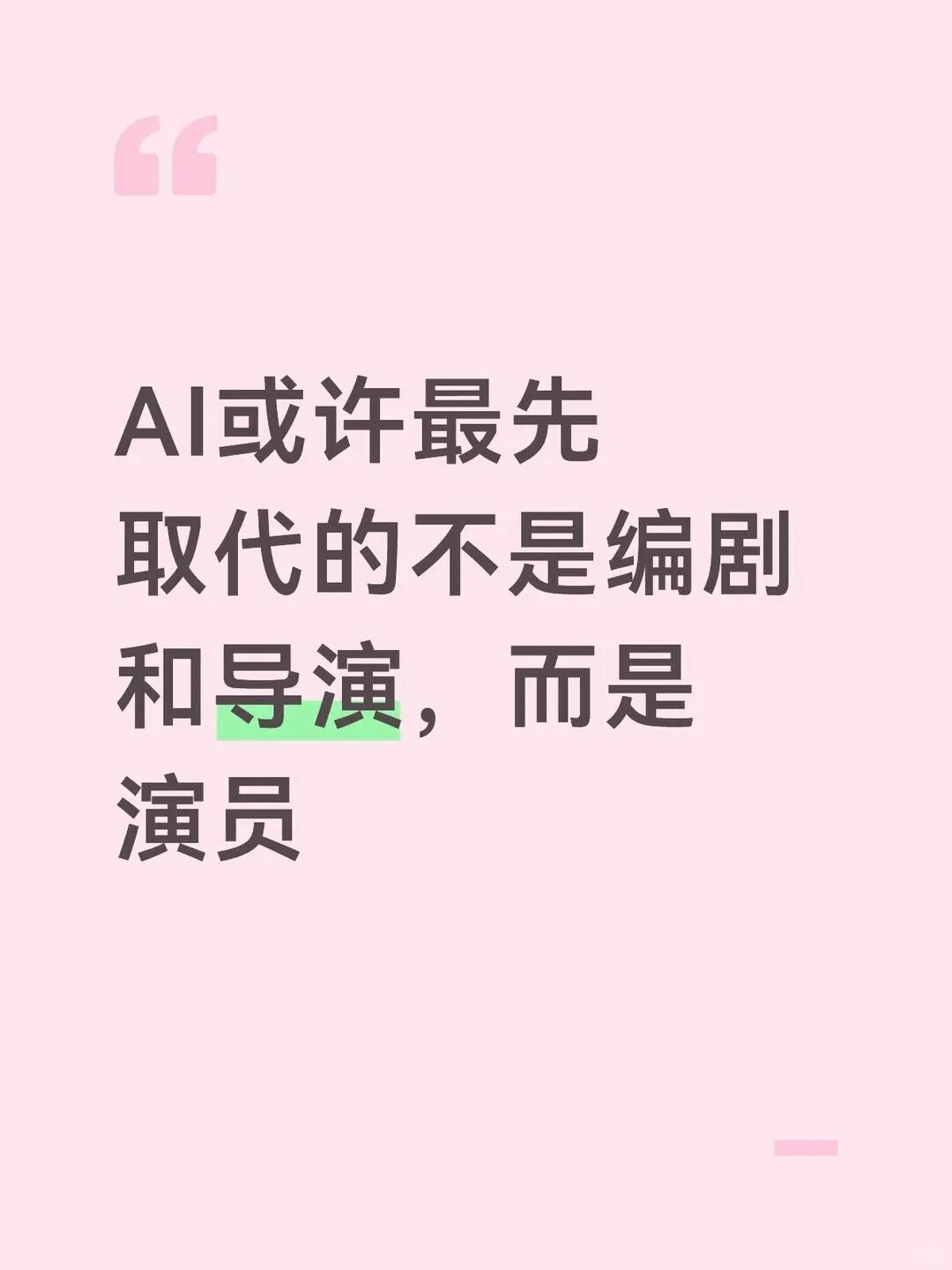
“替代”的另一面,那些能够驾驭AI工具、理解AI生产模式的影视从业者,正在成为新规则的定义者。
吴磊的乐观建立在“艺术平权”的判断上。他相信技术必然会降低准入门槛,有想法、有能力的创作者能借此快速将构思落地,圈子和资历不再能成为行业壁垒。“‘线上剧组’‘一个人的剧组’已经出现,人员更加精简,派系斗争、关系网复杂、人际内耗等长期困扰创作的附加成本也将随之消解。”小花则强调相似的“showrunner模式”,即编导一体的超级个人IP,“以后肯定是厉害的产品经理的天下。”
哈尼则把未来稀缺的人才分为两类:懂故事创作的小说作者、编剧,以及拥有绝佳视听审美的导演、画手。“技术平权,拼的就是谁的故事更动人,谁的脑洞更大,卷内容、卷审美。”她勾勒出一支“特种部队”的雏形:拥有创作能力的编剧+具备审美和优化文本能力的AI导演+负责SOP工作流的执行技术人员+AI算力。这套精悍的编制将颠覆传统影视动辄上百人的庞杂体系。
更颠覆的是成本结构:“以前拍一部45分钟×40集的电视剧可能要耗费数亿,AI电视剧纯制作成本可能只要几万块。”她甚至设想了一种预演:AI也可以先跑一遍剧本,将准备真人实拍的项目可视化,内容好坏一目了然。“有些编剧只是名气比较大,其实写的剧本真的不合格,但平台就是会盲目买单。”

技术让旧边界——譬如资本、设备、人脉、资历——日渐模糊,也同时竖起了一道更高的门槛:审美、判断力、叙事能力。哈尼坚信:“天才绝对不会再被埋没。”当AI飞速发展倒逼传统产业成长,技术正在做一件老派的事情:把创作还给创作者。
迷雾中找未来
当然,Seedance 2.0的“言出法随”,也带来了一系列尚无法可依的伦理难题。
吴磊用一个朴素的比喻回应了这一困境:“AI视频生成目前还处在孩童阶段。”在他看来,海量素材是AI成长的必经之途,但“要像教育孩子一样教育AI,有选择地让它接触复杂的真实世界,为其设立边界”。哈尼则坦言,AI模型“学习参考”与“掠夺个人资产”的界限十分微妙,“就像影视作品里的致敬和抄袭有区别,但目前仍是一片灰色地带。”她强调,“版权界定和数据使用的确权必须跟上”,这是技术狂奔时绝不能省略的刹车系统。
两人都承认“参考”的必要性,却也都清醒地注视着那条正在模糊的界线。而小花则直接点出“AI侵权”的风险,认为如果缺乏规制,中国恐将滑向一个“山寨大国”。在她看来,未经确权的数据喂养并非“学习”,而是“满足没有才华的小偷的虚荣心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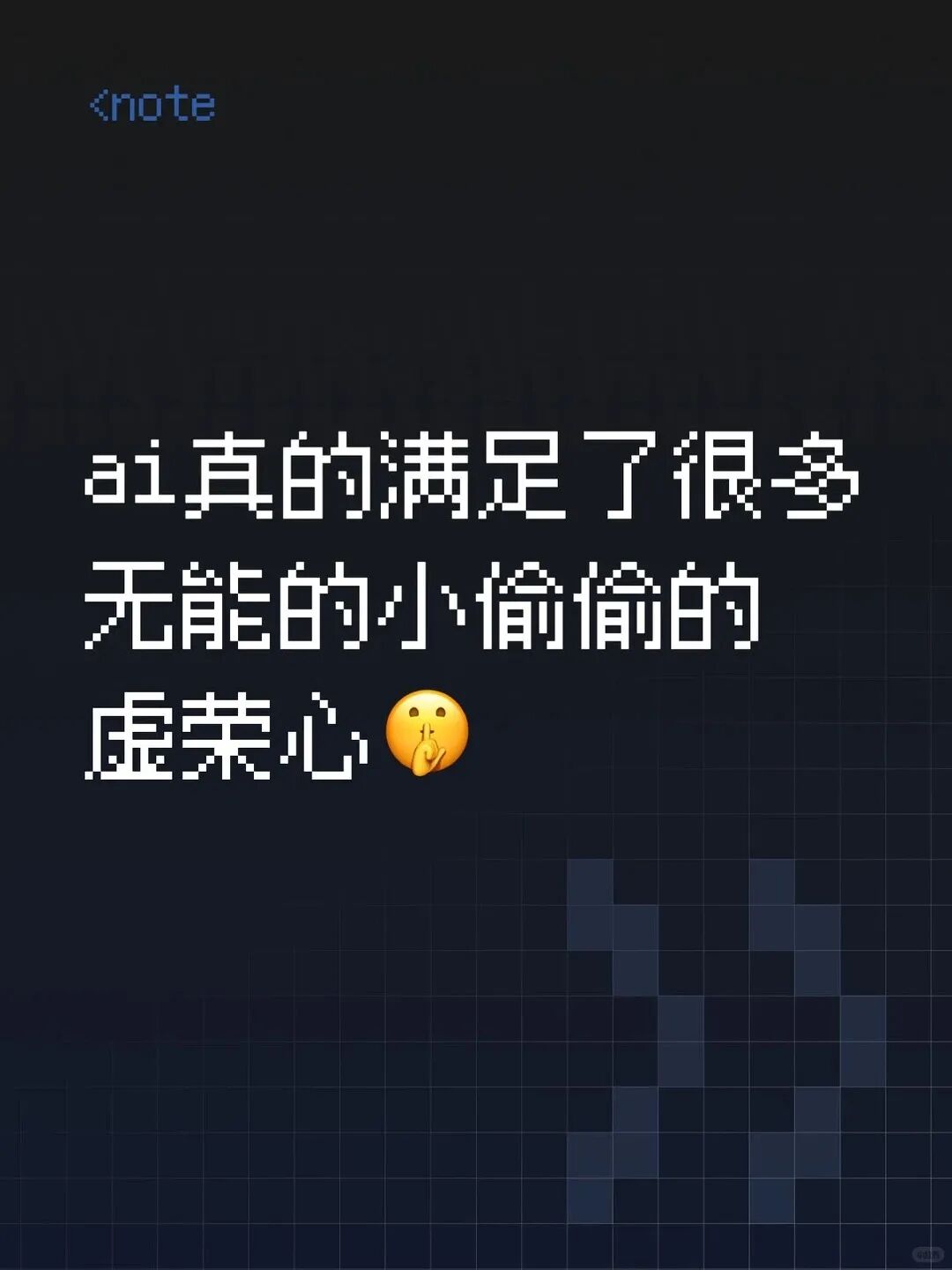
争议不止于版权,更触及一个根本问题:当AI能够高速生成影像,它究竟是在“创造”,还是在“杂糅”?
吴磊将当前AI工具定位在“杂糅”阶段,“其技术底层逻辑是海量数据的积累和根据提示词的排列拼接组合”,但他补充说,这样的生成内容“并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”。哈尼的回答斩钉截铁:“AI的底层逻辑永远是模仿,很难创新和创造。”她指出,无论剧本还是分镜,AI输出的都是“大概率”内容,而“艺术的底层逻辑是“意外”,“是人性的不讲道理,讲究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”。
工具越强大,“人的独特创意”会成为唯一的护城河,作者性或许不会被削弱,只会被无限放大。
而小花的忧虑恰在于此,当创意可以被高速复制,稀缺性便不复存在。“作者想出一个创意,需要大量的阅读、积累、思考、体验、观察,还要有天赋、敏感度,”她说,“AI直接抄走、批量生产,创意就会变得很廉价。”她以竖屏短剧为例,“短短两年间,这个赛道榨干了网文二十年来所有的精华梗,导致长剧和电影拍什么都不新鲜。”

众多顾虑下,影视行业究竟会走向何方?
吴磊预测,“AI视频生成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,会如同网上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一般。影视城、器材租赁、群演配套等传统产业链要素将变得不再重要,用工需求大幅减少,资金与人才将向新领域流动。”
哈尼的估计更为量化:传统影视如果不向“极致的情感体验和顶级实境美学”转型,市场份额“估计会被挤压到只剩三成”。但她同时也看到了另一条路径。作为科班出身、在剧组摸爬滚打近十年的从业者,哈尼坦言自己曾深陷“行业螺丝钉”的无力感。“可能你早已懂视听语言,却很难证明自己,需要慢慢熬资历才有话语权。”而AI将技术门槛降至“小白”级别之后,她惊讶地发现,自己过去十年积累的那些技能,在AI的辅助下完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她称之为“一飞冲天”。
技术的进步未必能够马上让思想文化艺术得到立刻的提升,更重要的是能用这个新的技术究竟能做什么。小花将AI比作“西贝的预制菜——花大价钱吃料理包加热的2岁西兰花,还说这是科技进步、与时俱进?”也警惕“注意力经济全面崩塌”的可能,认为资本与技术合谋的结果,并非普惠。
哈尼或许最能理解这种警惕,但她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:不否认风险,也期待确权与规制,更在意那个等了近十年才等到的机会。“我之前时常沮丧,因为有心无力,因为我知道我的故事想法,无法直面大众,”她说,“现在,我可以了。”
“AI巨浪袭来,不必惧怕惊涛骇浪,请尽情顺势而为。”既是AI创作者对时代的回应,也是对自己的交代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