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是地球历史上最值钱的上市公司?
英伟达么?
的确,在刚刚过去的10月,英伟达一度突破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,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市值最高的公司,总规模一度接近苹果和特斯拉的总和。
但英伟达其实不是人类历史上市值最高的公司。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,人类历史上市值最庞大的公司其实诞生在三百多年前的阿姆斯特丹:荷兰东印度公司(VOC)。
VOC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制公司,它在世界最早的证券交易所“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”上市,最高市值达到 7800 万荷兰盾。许多研究机构认为,这个估值相当于7.9万亿美元甚至更高(这些本身也都是10年前的预估,而近年美元通胀也很夸张)。有研究认为,这数字大概能占到当时荷兰共和国GDP的三分之二。
荷兰曾经是欧罗巴大陆的“美国”。
作为海上马车夫,荷兰人几乎垄断了香料贸易,因此它的人均GDP、技术水平、商贸体量、金融成熟度都大幅领先于英国等其他欧洲强国。欧洲的外贸结算货币也是以荷兰盾为主导,阿姆斯特丹更是全球的移民中心。
相比之下,美国今年的GDP预计将突破30万亿美元,英伟达市值目前大概占其总GDP的六分之一。但它已经是最接近VOC神话的当代公司了。
历史告诉我们,当一个公司到达如此体量,它背后往往意味着某种垄断性质的支配级力量。
就像英伟达在AGI世界里也有无数的美名:
显卡央行、算力美联储。
如果说“算力”是AGI世界里的“货币”。英特尔可能是这个世界里的英镑,头戴的是顶生了铁锈的皇冠;博通可能想力争成为欧元,以“合纵”来抗“连横”;那么英伟达便是美元级别的存在。
什么是美元级别的存在?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:
铸币权

所谓“铸币权”,不仅是发行货币的资格,更是从发行货币中获得收益的权力。它的发行量决定了货币量,决定了究竟是通货膨胀还是紧缩,决定了货币贬值的速度,那么它就在区域内拥有了支配级的地位。而当这种权力越过区域变成全球的强制性存在,把我们便可以说,它是一种:“美元级别”的存在。
而如果抛Web3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存在不谈,上一家拥有铸币权的商业性公司是谁?
东印度公司们。
与主权货币不同,美联储和央行们最常标榜的是“政策中立”,因此发行的货币也是“中立”的。但东印度公司们不是。
他们具备更强势的一面:他们不仅发行货币,还决定货币的流向。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投资、放贷、购买商品,以货币为锚点,在当地构建自己的经济体系。
就像今天的英伟达一样。
以算力权力为锚点,今天大量硅谷的明星AI生态公司都已经直接或者变相与英伟达建立了双重关系:英伟达是他们的股东,他们是英伟达的客户。
英伟达以现金方式入股这些公司,然后这些公司集合其他所有股东的钱,再去银行或者孙正义那里做一笔杠杆交易,最后捧着更多的现金来购买英伟达的显卡。而如果一家公司不是英伟达的客户或供应链伙伴,那它大概率也很难拿到英伟达的投资——因为他们缺少共同的愿景。
作为今天硅谷出手规模最大的AI投资者,英伟达近年已经在投资并购上披露了至少1500亿美元的计划,如果算上美国的芯片基础设施投资承诺,这一数字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。目前,它的投资版图包括但不限于:
- AI公司:OpenAI(1000亿美元)、xAI(20亿美元)、Mistral AI、Perpleixity、Safe Superintelligence、Runway、Cohere、Thinking Machines Lab、Reflection AI、Scale AI、Poolside、Sakana AI、Kore.ai……
- 芯片相关:英特尔(50亿美元)、Ayar Labs、Enfabrica……
- 云或垂直场景:诺基亚(10亿美元)、CoreWeave、Nscale、Lambda Labs、Bright Machines……
- 机器人与自动驾驶:Figure AI、Wayve、Nuro……
- 前沿技术(量子计算与核聚变等):PsiQuantum、Quantinuum、Commonwealth Fusion……
在英伟达的投资版图里,你可以看见AGI的当下与未来。
这有点像一套英伟达版本的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与“马歇尔计划”。

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全球经济秩序——以美元为锚、通过规则、结算体系与金融基础设施机构们把世界绑定在美元框架内。而马歇尔计划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,以美元投资来推动整个欧洲的战后重建,形成一个繁荣但以美元为中心的西方经济。
英伟达本质也是一种AGI秩序——以GPU为锚、以CUDA为规则、通过庞大的算力生态联盟,将AGI嵌入到英伟达的框架里。再利用针对性的对外投资,扶持一个繁荣但以英伟达为中心的AGI科技体系。
对于英伟达而言,AGI大概像一个广阔的商业处女地。它踏入AGI时的心情,甚至大概与东印度公司踏入印度时的激动是相似的:
一方面,它面对的是一个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刚刚交汇的时间窗口,所以这片土地一切迈向现代化的红利都与它有关,有着全世界最有想象力的商业故事;
另一方面,东印度公司不是慈善组织,而是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商业实体。殖民地的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利润表,利润的前提是成为殖民者更庞大的市场和更高效率的原材料工厂。它需要控制更多的经济体系,派驻更多的士兵,维护以重商主义为典型代表的单边贸易秩序。
而对英伟达来说,AGI与它的关系也是类似的:
一方面,英伟达需要推动整个AGI生态的成长,因为这是它的利基市场。某种程度上,后者的成长性,决定了前者的估值水平。另一方面,AGI生态的惯性也是它的武器,它会进一步推动以英伟达CUDA技术栈为基础的生态繁荣,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业务的护城河。
为了维护铸币权,东印度公司靠枪炮,他们把印度士兵从南亚运到全球各个角落的殖民地;而英伟达靠CUDA,他们把全球的开发者都绑定在自己的工具生态里。
随着AI叙事的兴起,今天CUDA的统治力,甚至超过了很多当年英伟达支持者的想象力:
从2007年CUDA项目成立到2019年的十二年时间里,CUDA生态总共累计了160万名开发者。
而到了2024年6月,黄仁勋宣布CUDA的开发者就超过了500万名。
在CUDA积累的智力资源越多,英伟达就越不可能被挑战。而今天只要在AI开发和训练领域,几乎没有人能真正绕过CUDA。巨头们为了在推理层面降低对英伟达的依赖,甚至不得不采购博通用ASIC方案(定制芯片服务),但却依然无法真正摆脱由于生态绑定对英伟达的依赖。
今天,英伟达和博通可能是世界五百强里毛利率和净利率最高的“设备公司”。其中,英伟达盈利能力最高,毛利率达到了75%,净利率达到56%。
作为对比,苹果的净利润率只有26%,AMD只有22%,英特尔则已经陷入亏损。
“数据殖民者”

当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,它的初衷并不是一个准主权实体,并没有铸币权和外交权,而只是一个商贸的联合体。
但是随着在殖民地的商业利益的不断深入,不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竞争不断白热化,拥有近似主权的能力成为了这些公司持续获得利益增长的内在要求。
这就像OpenAI诞生之初,其实仅仅只是一个面向AGI的、具有某种乌托邦式的探索性质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。而历史上,首批以官方身份来到东亚的欧洲人也大多是虔诚的牧师,在一百年后慢慢变成了殖民军队。
如果说英伟达是荷兰东印度公司(VOC),那么OpenAI则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(EIC):
首先,EIC的盈利能力不如VOC。因为VOC掌握了最值钱的香料产业,而EIC争夺不力,在东亚地区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鸦片;
其次,VOC控制了很多航运中寸土寸金的岛屿和港口城市,比如马六甲海峡、巽他海峡等。而EIC则控制了没那么赚钱,但是潜力无穷、人口众多的印度次大陆。
最后,EIC还需要从VOC手里高价购买大量的香料,作为船只的过路费。
这刚好是英伟达与OpenAI之间“竞合”关系的真实写照。
英伟达在产业上游,掌握利润最高的要塞堡垒,构筑全行业最高现金流的护城河;
OpenAI与英伟达保持和睦,每年还要向英伟达采购大量的算力设备来维持竞争力,但同时与AMD和博通合作,不放弃向对上游影响力。同时,OpenAI的主战场还要面向最广阔的市场腹地,做潜力最大、管理难度最大的C端市场。此外,OpenAI还透露,将在今年底跟进“成人模式”,从而放开更多色情和暴力内容的消费限制。
而在印度,三百年后的今天,OpenAI们也正在重新定义了西方国家与南方国家在AGI上的“剪刀差”关系。
在EIC时期,西方与印度的关系是:西方从印度拿走原材料,输出工业制品;而在AGI时期,西方正在从印度免费拿走数据、训练,再用印度廉价的工程师打标注,最后把AI能力返销给印度。
今天,“数据殖民主义”、“数据版的东印度公司”已经是许多印度政客和学者在讨论的话题。
与移动互联网时期讨论的“数字殖民主义”不同,这次AI浪潮带来的数字化能力会直接嵌入工作流里,可能导致大量的处级工作被替代。而这类工作显然在南方国家占比会更多,且社会往往缺乏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。这必然会导致“数字殖民主义”的问题更加紧迫。
印度前IT部长Ravi Shankar Prasad就多次提出,不能让美国互联网巨头“像东印度公司一样工作”。而对“数据殖民主义”的担忧,也在不断推动印度去做修法,来保护国家的数据安全,要求更多的云算力部署在印度本土。
但从中长期来看,这种“数字殖民主义”比坚船利炮更隐形,它来自一种结构性的资源和科学水平差异,其实很难完全避免。
以数据为例,由于缺乏像欧洲那样完整的数据保护法律法规,印度政府和用户要起诉OpenAI会更加艰难。当然,印度本身也很难在司法层面举证,表示哪些数据来源于印度互联网,提供了多大程度的贡献,带来了多大程度的损失。因此,在全球范围内,起诉大模型公司数据滥用的胜诉案件至今凤毛麟角,还主要集中在整体获益于AI的欧美地区。
而在技术层面,拥有像DeepSeek、Qwen、Mistreal那样具备主权能力的AI大模型,其实是印度的最优解。
但那意味着庞大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庞大且顶级工程师团队加持。我们姑且不说,大量的GPU采购本身也要来自英伟达等硅谷芯片公司;庞大的电费开支,在一个电网脆弱社区,也往往意味着更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。
更何况,AI是一个高度竞争的商业竞赛,往往是赢家通吃的平台级竞争。即便像Mistreal AI这样含着金钥匙的欧洲主权AI,但今天的模型表现也不尽如人意。
目前印度正在把目光投向中国的开源模型,他们希望在DeepSeek的基础上来fine-tune一个印度自己的主权AI大模型。但AGI是一个庞大的生态,一个fine-tune的大模型只能解近渴,却不足以跳出被动的生态位。
不过这再次体现了今天开源生态的重要意义,没有普惠开放的AI可能是危险的。
“泡沫”

与AGI相比,投资者对东印度公司的信仰是更加牢不可破的。
它有国家背书,有两百年稳定的高分红历史,有殖民地可观且稳定的增长愿景。
东印度公司股票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今天美国的养老金体系(401K)。在当年“无脑”定投东印度公司,就相当于今天“无脑”定投的纳斯达克指数。既有稳定的股息收益,还有长期的市值增长。
因为在垄断经济下,东印度公司天然就是一个估值的放大器:
垄断收益会放大资产现金流背后的收益率。
国家信用会降低系统对风险的折现。
而增长愿景会催生更乐观的投资情绪。
在著名的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中,南海公司仅仅只是放出与政府深度合作的假象,就成功拉动公司市值在很短的时间内,暴涨了近10倍。
东印度公司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二级市场泡沫神话,直到AGI的到来。
AGI的支持者总是拿世纪之交的.com泡沫和今天的泡沫对比,以此论证AGI的泡沫只是阶段性的。毕竟相比于当年动辄200倍的PE,英伟达50多倍的动态市盈率显得非常温和。
但这忽略了AGI泡沫下巨大的市值规模。
如果我们把2019年和2025年的硅谷市值排名做一个对比:
2019年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四家公司在万亿美金左右,Meta则大约5000亿,紧随其后的是思科、英特尔,大约在2000亿美金以上,英伟达、甲骨文、奈飞、IBM则在千亿美金俱乐部,代表性的头部公司的总市值预计在6万亿美元。
彼时美国GDP为21万亿美元。
而到了2025年,英伟达市值突破5万亿、苹果与微软站上4万亿,谷歌3万亿,亚马逊2万亿,Meta、博通、特斯拉分别超万亿,还有甲骨文、奈飞、palantir在5000亿左右,AMD超4000亿美元,美国头部科技公司的总市值大约在25万亿+美元。纳斯达克今年也以36万亿+美元的规模历史性超越了纽交所。
而去年美国的GDP为29万亿美元。
如果说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国家的“商贸复合体”。如果将整个硅谷看作美国的“科技复合体”,那么今天这艘巨轮的市值成就已经超过了当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了。
如果打开英伟达们的股东名单,会发现有超过20%指数型定投基金,他们背后是包括401K和大量欧美日的养老基金与个人储蓄。如果按照纳斯达克36万亿美元市值计算,今天这些科技公司里至少有8万亿美元的定期储蓄资金。其中,仅英伟达一家就超过一万亿美元。
今天许多投资人没有说出口的逻辑是:
AGI的终局很有可能就是有垄断性的寡头天下。它会是过去PC时代谷歌、脸书、亚马逊们和英特尔的超级版本:覆盖率更广、渗入社会的程度更深、盈利能力更强、护城河更显著。
而坏消息是,这种竞争态势在今天似乎越来越明显:小公司小国家无法承担巨额的投入成本,也就无法参与游戏竞争。而能力差异和网络效率,又会搭建生产力和社交应用的生态护城河,于是重新演绎一遍过去的互联网往事。
“主权AI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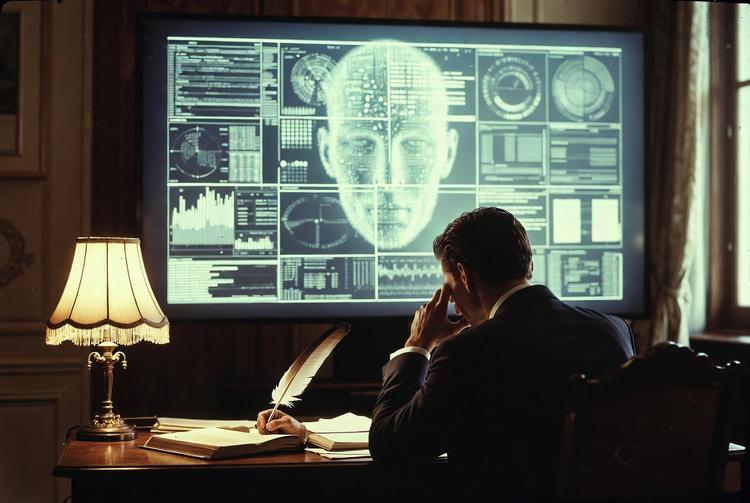
前段时间,微软CEO萨提亚在一个播客上抱怨:
他说,今天已经不再是显卡不够的问题了,而是有显卡,但是没有足够的数据中心存放,没有足够的电力系统支持。
而在刚刚过去的腾讯财报会上,马化腾也在抱怨:
他说,由于高端芯片受限,所以腾讯的Capex投入低于此前的数据指引。
黄仁勋频繁来往中美,在美国频繁强调中国的芯片与AI进展,希望让英伟达的芯片重新回到中国市场。他绝不希望中国成长起来一个可以平行于CUDA的开发者生态。
但今天所有人知道,英伟达必须服从美国政府的旨意,完完全全按照美国政府的主权意志来进行自己的生意——英伟达的能力是美国政府意志的工具,英伟达的影响力是美国全球权力的延伸。
这不是黄仁勋能够解决的问题。就像英国要求EIC向荷兰贸易禁运,虽然会导致生意受影响,但EIC也必须遵守。
10月,英伟达首次把GTC的大会地址选在了美国政 治中心华盛顿。那时特朗普已经启程去了APEC,黄仁勋对着空空荡荡的白宫讲了很多故事。
他说,英伟达的芯片已经在亚利桑那州的芯片工厂投产;他推出了量子计算机和超级芯片,讲了6G AI-RAN如何改变世界,此外,他还官宣了美国AI 超级工厂计划。
黄仁勋讲述这个计划的方式与总统先生的喜好如出一辙:
他将与美国著名红顶商人甲骨文公司、美国能源部合作,打造“Equinox"的站点来提供庞大的AI算力。此外,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将部署两台基于Nvidia Vera Rubin平台构建的下一代超级计算机,专门用于国家安全和开放科学研究。
英伟达说,AI工厂如何大规模生成智能,而未来也可以成为推动国家再工业化的抓手。
OpenAI也同样承载了美国的国家意志。
比如今年5月份,OpenAI推出了一个OpenAI for countries的业务。
OpenAI为这项业务写了一段很长的博客,而这篇介绍性博客的开头是这样的:
我们于一月与川普总统、合作伙伴甲骨文和软银共同宣布的星际之门项目已正式启动。这是史无前例的美国AI 基礎設施投资计划,首座超级运算园区在德州的阿比林市(Abilene)设立,预计未来将拓展更多。
我们收到来自各国的请求,希望我們协助打造类似星际之门的AI 基礎設施和相关專案……
我们希望为各国提供协助,同时推广民主AI,即在AI的开发、应用和部署过程中,实践并融入历久不衰的民主原则。
而在这篇博客的引言里,也毫不意外地写着:
“协助各国打造符合民主价值的AI发展框架的新方案。”
在OpenAI的计划的官方中文译本里,它表示希望首批与十个国家或地区一起,在整个项目做四个方面的努力:
第一,共建算力中心来保障各国的数据主权;第二,“为人民提供量身打造的ChatGPT”,来提高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效率,贴近当地文化;第三,筹措和运营国家创业基金,孕育国家AI生态系统;第四,合作国也将投入资源,推动全球星际之门项目的扩大,进而巩固美国在AI领域的领导地位,并促进民主AI全球网络效应持续发化。
在AGI时代,你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叙事:
OpenAI与英伟达本身是一种主权AI,它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意志。而当以OpenAI发轫的AGI革命,让更多国家意识主权AI重要性的时候,主权AI又成为了OpenAI们的生意。

英伟达去年也开始力推“主权AI”的概念。
对于英伟达来说,如果每个国家各自建设一个数据中心,那也是一笔不小的生意。去年“主权AI”业务给英伟达带来了100亿美金,今年则预计翻倍增长至200亿美金。有分析师认为,未来这项业务可能每年带来上千亿美金的收入。
而“主权AI”也不止是数据中心,比如我们此前写过的6G AI业务中,英伟达也将“主权基础设施”业务放在了重要的顶层菜单栏里。

对于这些国家来说,“主权AI”是一个诱人的概念。
它意味着更多的基础设施会在本地投产,算力设施更加可控,如果使用在本国部署的“定制GPT”,在数据保护方面也有更高的可靠性。
但它其实终究没有跳出几大头部科技公司的范围,利润的主体依然是流向它们的,更不用说它们本身也是美国主权AI的服务者。相比于真正独立的主权AI,这更像是贩卖一种主权AI的“特许经营权”,以更隐晦和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获取。
结语
东印度公司的血腥模式已经离我们远去了。毫无疑问,今天的国际秩序比殖民时期要好得多,各国主权的受尊重程度也远超过300年前的丛林时代。
但为何世界对殖民主义的讨论却从未停息过?
我们该怎么定义新时代“殖民主义”?在AGI的时代里,我想大概是两个国家实体的交易之中,他们所获得的利益与付出的成本、承担的风险和收益,都产生了极大错配。
AGI产生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“赢家通吃”的可能性,并且正在朝着一种超级巨头的生态大步向前——
这对全球都是系统性风险,但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,这种风险还要大得多。
而对于普通人来说,超级巨头与我们的关系也是值得深思的:
比如,这些AI拿走了人类所有的数据资产,用来构建一个庞大的生产机器,却从未真正为人类文明付过费。他们是人类存量数据资源的真正掠夺者。
而正如诸多AI学者所警告的那样,这些公司创造的产品可能产生“文明级”的风险,轻则导致大量失业、能源紧缺和价格上涨,重则导致文明的毁灭。这些风险是全人类共担的,但潜在的未来收益却都进入了这些巨头的口袋里。
这些何尝又不是一种数字殖民主义的翻版?





